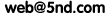歌曲 1
專輯
名 稱:
所屬區(qū)域:港澳臺(tái)
某天錄音室之后,阿升不想先回家,跑到一個(gè)叫ROXY IV的pub吃酒。有個(gè)很像“兄弟”的人跑來(lái)向阿升仔說(shuō):“我有些東西,要你聽(tīng)聽(tīng)!” 阿煜,1960年8月20日生于苗栗頭份,未婚。O型獅子座,排行老大,私立聯(lián)合二專機(jī)械科設(shè)計(jì)組畢業(yè)。服役前后總共換了十七個(gè)工作。 「都是酒精作祟啦。反正這種人又不是沒(méi)碰過(guò),還不是第二天就沒(méi)消息。嘿!沒(méi)想到第二天他真的來(lái)找我。」「其實(shí)我每天都把我作品的試聽(tīng)?zhēng)Х派砩?可是那天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,我第二天就去找他,就這樣。」 這個(gè)寒冷的夜,阿煜把他的音樂(lè)交給一個(gè)中國(guó)臺(tái)灣蠻子,自己走在遠(yuǎn)遠(yuǎn)的一角,不安地?fù)芘鑱y的頭發(fā)。阿升蹲坐在辦公室的音響前,聆聽(tīng)著那個(gè)土里土氣的老男孩的試唱帶。這是…客家歌? 這張專輯后來(lái)如何如何地碰壁,就不必提了,反正還是出片了。且聽(tīng)阿升和阿煜他們?cè)趺凑f(shuō)…… ■ 升:“原來(lái)叫‘寶島合唱團(tuán)’后來(lái)遇到高人指點(diǎn):現(xiàn)在應(yīng)該是‘新’寶島了!想想也是,我們所作、所唱的都是現(xiàn)在的中國(guó)臺(tái)灣,早就不是原來(lái)那個(gè)寶島了。我也搞不清 楚為什么會(huì)變成‘康樂(lè)隊(duì)’?像‘賣唱’、‘王祿仔’、‘歌劇團(tuán)’一樣都有討生活的意味。我們唱歌、作音樂(lè)也是在‘賺食’嘛。” ■ 煜:“我覺(jué)得不是講臺(tái)語(yǔ)就是中國(guó)臺(tái)灣人,我覺(jué)得你在這長(zhǎng)大就是這的人,土地是重要的。” ■ 升:“這就是中國(guó)臺(tái)灣啊!中國(guó)臺(tái)灣不一直都是這樣?在我的創(chuàng)作選輯里,我們的音樂(lè)就是一種生活,我們采揭的對(duì)象就是來(lái)自周邊的人……我們從來(lái)不打算給人家任何跟政 治、教育、執(zhí)政者抵觸的東西,我們只準(zhǔn)備告訴人家一個(gè)事實(shí)而已,我們?cè)趺椿钪褪窃鯓印槭裁创蠹叶疾辉敢馊ッ鎸?duì)事實(shí)呢?” ■ 煜:“…除了會(huì)講客家話;對(duì)所謂的客家也沒(méi)有什么了解,我們都是鄉(xiāng)下人不會(huì)去想這些,父母也不會(huì)去提醒你是客家人,也許知識(shí)分子(政客?)會(huì)吧?一直到我 開(kāi)始寫(xiě)客家歌,我才真正去接近一些客家素材。我真正意識(shí)到語(yǔ)言是很重要的,語(yǔ)言里面不知不覺(jué)會(huì)傳達(dá)一些沒(méi)被記載下的文化。不是因?yàn)槲覍?xiě)客家歌就表示我對(duì)客 家文化有多了解,只不過(guò)我是客家人,我會(huì)客家話……說(shuō)使命感沒(méi)有是假的,但講多沒(méi)有意義。現(xiàn)在有很多客家人組織、機(jī)構(gòu)要為客家人爭(zhēng)認(rèn)同,可使用一些比較 硬、比較嚴(yán)肅的方法要人接受是比較難的——或許音樂(lè)比較容易吧!” ■ 升:“其實(shí)我跟很多人一樣,本來(lái)對(duì)客家人是有一些成見(jiàn)的。接觸之后有了更多的了解,覺(jué)得其實(shí)牽涉的不只那么單純。有太多的地理、心理、時(shí)代因素在里面…… 有了解就會(huì)覺(jué)得還不都是人?沒(méi)有好壞之有不同。有一個(gè)笑話說(shuō)有個(gè)人說(shuō):‘我生平那個(gè)最討厭兩種人,一種人是有種族歧視的人,另一種人是黑人’。其實(shí)很多成 見(jiàn)是我們不自知的。中國(guó)臺(tái)灣那么小更應(yīng)該彼此多了解,我想就從音樂(lè)開(kāi)始吧!” 更多>>